專訪0G創辦人Michael Heinrich:讓AI成為公共產品
隨著主網正式上線,0G 進入了新的階段。它已擁有超過 100 個生態夥伴、8,880 萬美元的生態基金,以及一支融合東西方背景的團隊,為實現宏大願景奠定了基礎。
9 月 22 日,0G Labs 正式上網主網,這個被稱為「首個模組化 AI 鏈」的項目,終於進入了主網時代。幾乎同時,納斯達克上市公司 Flora Growth 宣布完成 4.01 億美元融資,用於啟動 0G 的財庫策略。
自創立起,0G 就因其技術突破而受到廣泛關注。透過模組化架構與革命性的資料可用性(DA)方案,0G 能以比競爭對手更低成本、更快的速度,處理 AI 應用所需的大量資料。而在科技之外,0G 更重要的標籤是其願景,讓 AI 成為公共物品,建構一個開放、可驗證、去中心化的 AI 生態系統。在巨頭林立、黑箱化嚴重的當下,這個願景格外稀缺。
計畫背後的創辦人 Michael Heinrich 本身就是個很有故事的人。他出生於烏克蘭,在東柏林長大,後移居美國,成為史丹佛學者。從微軟、貝恩、橋水等頂尖機構的精英,到連續創業者,他的人生軌跡橫跨科技、金融與教育。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0G 與中文社群有著深厚淵源。行銷長 Ada 來自湖南長沙,同時也是 Michael 的妻子;技術核心成員 Fan Long 與 Ming Wu 曾是中國公鏈 Conflux 的共同創辦人;甚至連 0G 的熊貓吉祥物,也源自於 Michael 十餘年少林功夫練習得來的「功夫熊貓暱稱」。這種東西方文化的深度融合,為 0G 的全球化發展增添了獨特優勢。
在主網上線的關鍵時刻,律動 BlockBeats 與 Michael Heinrich 進行了一次深度對話,探討他的個人成長經歷、0G 的技術創新與競爭優勢,以及項目與中文社區的特殊淵源。
跨文化成長塑造的獨特視野
Michael Heinrich 的人生軌跡始於一個劇烈變革的年代。他出生於烏克蘭,在東柏林度過童年,13 歲時移居美國。跨文化遷徙本就罕見,而他不僅順利適應,也從中提煉出對身份與環境的深刻認知,這些經驗深刻塑造了他此後的思維方式和創業理念。
從微軟、貝恩諮詢到橋水基金,Michael 先後在不同領域的頂尖機構歷練,累積了橫跨科技、商業與金融的全方位經驗。從「證明自己」的外在驅動力,到「尋找價值」的內在探索,他一步步完成了職業上的跨界躍遷,也為日後創業奠定了基礎。
更有趣的是,他曾在史丹佛大學開設課程“Hacking Consciousness(破解意識)”,並被評為 iTunes U 2014 年度最佳課程。這門課探討意識、科技與人類福祉的關係,從某種意義上,也與他如今推動的去中心化 AI 理念存在著深層呼應。
律動 BlockBeats:您出生於烏克蘭,在東柏林長大,之後移居美國,有哪些經歷改變了你,這樣的跨文化經驗對您後來的思維方式和選擇有哪些影響?
Michael:首先,我發現自己能夠看到人們在不同環境下的生活方式。讓我驚訝的是,人們的生活方式差異非常大。在柏林,文化氛圍更重視群體性,人們不像在美國那麼強調個人主義。在美國,個人主義更強,關係似乎更停留在表面,雖然廣泛,但真正深入的關係卻更少。
這樣的文化體驗在某種程度上塑造了我,讓我在來到美國時可以思考該如何展現自我、如何界定自己的身份。剛來美國的時候,我其實很掙扎。例如,我應該在超市對父母講英語,還是繼續講德語?我必須做出一個選擇。
當時我 13 歲,我甚至可以決定是否要保留口音。我要完全變得像美國人一樣,還是要保留一點歐洲的痕跡?我最後刻意選擇了保留一部分歐洲的文化特徵,因為如果我徹底融入環境、被完全視為「美國人」,我會覺得自己對成長經驗缺乏完整性。
比方說,我想要維持這種完整性,保留屬於自己的文化部分。另一個有趣的地方是,當時人們對來自東柏林的人仍有一些負面看法。所以一開始我會刻意隱藏自己來自東柏林的身份,有時甚至會說我是從西邊來的。但後來我覺得,這太荒謬了。我應該為自己的背景感到自豪,這是我無法改變的事實。如果別人因此對我有負面看法,那是他們需要解決的問題,而不是我。
在這個過程中,我學會如何塑造和守護自己的身分。
這點在我二十幾歲時再次體現。當時我上了一些課程,像是 Landmark Education,在那裡我意識到,我們內心的故事其實主導了我們在社會中的行為。例如,我曾經覺得父親總認為我不夠好,因此我必須表現得完美,讓他挑不出毛病,好配得上他的愛。後來我才明白,那完全只是我腦子裡的一個臆想。我們要學會處理這些臆想、理解我們內心賦予的意義,這樣我們才能為自己創造對社會和自己都更正面的現實。
總的來說,我學到的一點是:塑造身分認同、適應不同環境,做出我的選擇。
律動 BlockBeats:在微軟、貝恩、橋水這樣不同領域的頂尖機構工作過,是什麼驅動您不斷跨界探索?這些跨界的經驗有沒有讓您獲得某些能力或形成某種價值觀?對您後來創業產生了哪些影響?
Michael: 對我來說,在大學期間,我就想搞清楚自己真正的熱情在哪裡。我起步得比較早。我是在一所美德學校讀書的,那時候我大概十三、十四歲,常常去我父親的辦公室上網閒晃。後來有一位經理髮現了我,他說:「你乾脆做點有用的事情吧?」我問:「那我能做什麼呢?」他說:「不如學點編程,幫我們做點事。」我當時說自己不會,他說:「沒關係,我送你去訓練營,你就能學會了。」
四周之後,我去了一個 Visual Basic 的訓練營,學會了編程,並為 SAP實驗室開發了一些早期的 Web2 應用。因為我年紀太小,他們沒辦法付我薪水,就給了我很多免費的硬件,像是 ThinkPad 筆記本。那段時間特別有趣,我體會到了當工程師的感覺。但不知為何,我並沒有完全被滿足,我還想探索更多的領域,看看自己真正的興趣點在哪裡。
那時我受一種社會敘事影響,在想人們覺得什麼是體面的,什麼是最難進入的行業。於是我嘗試去微軟,試著管理諮詢,後來又去了全球最大的避險基金橋水。最初驅動我的是一種「我要證明自己足夠好」的心態,但在經歷 Landmark 課程之後,這種心態逐漸轉變成了:「我個人真正關心的是什麼?我想為世界貢獻什麼?」所以從「社會認為什麼有聲望」,逐漸轉變為「我認為什麼對社會是必要的」。這是一個重要的轉變。
同時,跨越這些不同領域,我累積了許多寶貴的技能。例如產品管理的能力,這在早期創業時尤其有價值,因為要弄清楚用戶真正想要什麼,再把它寫成一個有說服力的產品說明,然後快速測試 MVP 產品,最後能迅速把產品規模化。
在微軟和 SAP 的經驗讓我獲得了這類技能。而在貝恩則學到另一套技能,那就是如何在高階管理層面前展現有說服力的想法,如何拆解問題、分析問題,從而真正帶來長期的業務價值。
這套技能在創業後期、公司進入規模化階段時非常有用。但在創業早期就不適用,因為那個階段比較像是要測試和摸索可擴展的商業模式。如果一開始就花三個月去做複雜分析,反而會錯過機會,不如直接執行、跟一堆人交流、做個 MVP 嘗試才是正解。
至於橋水帶給我的能力,它對 Web3 尤其重要,因為這個領域高度依賴金融工程。對各類金融產品、結構化產品、交易運作、投資組合建構的深入理解,也影響了我對資金管理的思考。我們公司的一個核心價值就是要自我造血、自我永續。現在我們的資金管理策略幾乎可以抵銷全部的消耗,讓公司保持永續運作。
所以,這就是另一點收穫,不僅來自這些經歷,也來自我在 Garden 的經驗。我想後面還有一個相關問題,到時候可以再詳細說明。
律動 BlockBeats:您練習少林功夫超過十年,是什麼契機讓你接觸少林功夫的?功夫哲學是否有影響到你的生活或思考方式?
Michael: 大概在我 16 歲的時候,我已經提前進入大學了。那時有一門太極課,不知為什麼,我被那門課吸引了,就去試了一下。結果我愛上了它,一練就是好幾年。
我很享受太極帶來的好處,例如我感覺到身體裡充滿能量,能切實體驗到「氣」,甚至能讓手掌發熱。這種體驗和我在科學裡學到的完全不同。科學裡講能量是物質性的、有定義的,但身體裡的能量是另一種存在。正是這種「所學」與「所感」的差異讓我著迷。
後來,我逐漸停下了太極練習,但也一直在懷念那種感覺。
在二十幾歲時,離開橋水之後,我對自己說:“為什麼不把這種東西重新帶回生活裡?”
但這次我想找一些更具身體挑戰性的,因為雖然太極的能量流動讓我很享受,但我希望它對身體的負荷非常大,我希望它對身體的負荷非常享受,但它對身體的負荷。
有一天,我在探索頻道看到一位少林寺出走的僧侶的採訪,他當時恰好在紐約。他展現了少林功夫的技巧和訓練方式。我被震撼了,像是「寸拳」,科學家甚至在專門測量出它的衝擊力。我突然意識到,人體潛能還有很多是我沒體驗過的,於是被深深吸引,馬上去找了一個功夫館。最初的幾堂課特別殘酷,我累得要命,但堅持大約半年後,身體逐漸適應了。每次課後雖然很疲憊,卻無比清醒、專注。這種狀態讓我覺得,少林功夫簡直是創業家的完美鍛鍊。
它包含了有氧訓練,因為動作很快、節奏很強;你會不斷移動、打套路、用兵器;它也有力量訓練,因為有些兵器很重,需要長時間揮動;它有柔韌訓練,因為功夫的核心之一就是身體要靈活。所有訓練加起來,一個半小時就能完成全套。對我來說,這是最高強度的綜合訓練。它不僅鍛鍊身體,也把一些價值觀帶進了我的生活。
在紐約的時候,每次上課結束,師父都會說「聖誕快樂」「新年快樂」以及類似的佛教祝福。這教會了我無論生活裡發生什麼,都要用一種慶祝的心態去面對。因為你不知道眼前的事到底是好還是壞,只有在回頭看時,才能明白它是如何改變你的。
這種哲學一直影響著我,用一種慶祝的心態去接納一切,因為最終一切都是有益的。這是少林功夫給我最重要的啟發之一。
律動 BlockBeats:在創辦 Garten 的過程中,您經歷了從快速成長到因疫情遭遇重創的巨大波動。這段過山車般的經歷,為您現在領導 0G Labs 應對加密市場的波動性提供了哪些寶貴的經驗?
Michael: 2016 年我全職開始經營公司,入選了 Y Combinator,當時一切都在越來越好。
我們的收入從大約 300~400 萬美金增長到接近 1000 萬 ARR,那是一段極其出色的經歷。所有人都想投我們。我們完成了 500 萬的種子輪融資,之後又有更多投資人加入,最後 Garten 完成 2,000 萬美金的種子輪融資。
一切看起來都很順利,收入持續成長。第一年翻了兩倍,第二年三倍,之後又連續翻倍。到 2020 年,我還在董事會上說:「今年我們就能做好 IPO 的準備,明年我們就能上市。」我們有龐大的管理團隊,一切都朝著規模化的方向走。完全沒想到四周之後,我不得不裁掉 75% 的員工,因為新冠爆發了。這是我們完全沒有預測到的。
我以前在金融危機中學到的教訓是要隨時準備好應對不可預測的市場風險。例如當時我們不得不快速把資金從雷曼兄弟、餐飲等高風險部位撤出來。但這一次,新冠帶來的衝擊是徹底的、毀滅性的。幾個月內,我們失去了 95% 的收入,ARR 只剩下 500 萬。公司從順風順水,瞬間掉入深淵。那種感覺就像在駕駛一架飛機,突然一片漆黑,機組慌亂,發動機熄火,塔台也沒有回應,而我必須想辦法讓飛機安全降落。對創業者來說,這是最極端的考驗,因為那幾乎等於公司的「猝死」。
我們本來有一份 2000 萬美元的 term sheet,可以再撐好幾個月,但疫情一開始,那份 term sheet 就立刻被撤回。公司迅速從「現金充裕」變成「現金枯竭」。我們不得不以最快的速度削減成本,從 650 人裁到年底只剩 35 人。
這段經歷徹底塑造了我。它讓我下定決心,以後無論再創業甚麼,一開始就必須確保業務的可持續性。我會提前考慮最壞的情況與風險。在加密產業,這種風險甚至更明確,因為它有固定的四年週期。
所以這次在募資時,我就提前想好:「要撐過下一輪熊市,我需要多少資金?」我的原則是要融到超出最低需求的資金。結果我們本來只打算融 500 萬,但最後完成了 3,500 萬的種子輪融資。這讓我們無論經歷怎樣的熊市週期,都有足夠的資金存活下來。
同時,如我之前提到的,透過智慧的資金管理,我們基本上能抵銷掉所有的支出。這保證了協議的長期可持續性。
這樣我們才能真正以長期視角思考。因為我們的使命,把 AI 打造成公共產品,不是一兩年的目標,而是需要很長時間來建立生態。要看到 AI 如何真正改變社會,甚至 AGI 出現,機器人普及,那都不是短週期的事情,而需要很長的時間去實現。因此,我們必須以長期為導向來思考和行動。
律動 BlockBeats:您在史丹佛大學開設一門名為「Hacking Consciousness」的課程。這個課程的初衷是什麼?您希望學生從中獲得什麼?這與您現在創業所做的事情是否存在某種哲學上的關聯?
Michael: 最初的靈感其實要感謝我在橋水的同事 Riddle,他向我介紹了「超覺靜坐(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
起初我以為自己只是報了一個簡單的冥想課程,但很快發現其中有更深的東西。我開始接觸到一個我從未意識到的層次。課程的方法很簡單,每天兩次,每次 20 分鐘,不費力地重複一個咒語。然後它會帶你進入狀態,進入超越思考的狀態,在神經科學中被稱為「安靜而警覺」的狀態。
在那種狀態下,你會有一種「回家」的感覺,一種極度喜悅的狀態,幸福、安寧、內在的滿足與寂靜,種種特質都會出現。我之前從沒想到如此簡單的練習能有這麼強大的力量。它徹底改變了我的人生。我變得更清晰,能以一種第三維度的方式來感受自己,我知道「真正的我」既不是身體,也不是思想,而是背後的覺知。
透過連結這種覺知,我更認同「觀察者」的角色,而不僅僅是物質現實的存在。這種覺知與所有人相連,也帶來一種平靜。我能深切地感受到與環境、與他人的連結。我體驗過多種不同的意識狀態,在其中一切都變得更美麗、更明亮。就好像大部分時間都處於「愉悅的高點」,但這是自然的、正面的。
這種深刻的轉變讓我想把它帶給更多人。於是我創辦了「Hacking Consciousness」這門課,希望學生能體會到,在我們所見的物質世界之外,還有一個「意識維度」。我想透過課程引入這樣的觀點:意識才是一切,我們要換一個角度去理解世界。
這門課和我現在工作的哲學連結在於,如果我們希望社會能真正繁榮,就必須提升自我。如果 AI 將接管大量我們不願意做的工作,那麼人類還能做什麼?我們的神經系統使我們能夠「超越」,而未來我們將有更多時間把注意力放在「超越」上,直至達到自我實現、開悟,去體驗這些生命狀態。這樣我們會真正更幸福,而不是永遠追逐「下一個 100 倍回報」。更重要的是去追問:什麼才是真正屬於我的幸福?如何才能讓我在現實中成為最圓滿的自己?
把 AI 打造成公共產品,就是在為這種可能性鋪路。作為其中一部分,我也希望能激勵更多人去實踐這些技巧,例如超覺靜坐,以及其他形式的修行。
0G 的技術創新與競爭優勢
在區塊鏈與 AI 的交會點上,技術更新迭代極快,但真正能解決實際問題的突破並不多。 0G Labs 能在競爭激烈的賽道中脫穎而出,核心在於其獨特的技術架構與對 AI 應用痛點的深刻掌握。
0G 的關鍵創新是模組化架構。這種設計讓不同元件可以獨立優化與擴展,在效能、成本和安全性之間找到新的平衡。尤其在資料可用性(DA)領域,0G 提出了革命性的方案,以遠低於競爭對手的成本處理 AI 應用所需的大量資料。
更值得注意的是,0G 不只是一個技術平台,而是一個 生態系統的建構者。主網上線首日吸引了 100 多個生態夥伴,這在區塊鏈專案中極為罕見,背後體現出團隊對生態建設的長期思考與佈局。
律動 BlockBeats:0G 的定位是「第一個模組化 AI 公鏈」,能否用一個簡單的比喻,向非技術背景的聽眾解釋 0G 的模組化架構,以及它為什麼對 AI 如此重要?
Michael: 所謂模組化架構,可以這樣理解:如果用雕像來做比喻,你有兩種創作雕像方式。第一種是用一整塊水泥雕刻成型,那最後就只有一個固定的雕像。第二種方式是用一塊塊樂高積木拼成雕像。
如果用的是水泥塊,一旦雕好了,要修改幾乎是不可能的;但如果是樂高,你只需要拿掉幾塊,再換上新的,就能輕鬆調整。這就是模組化帶來的靈活性。它允許系統更客製化,你可以自由選擇對自己最合適的組件。
例如,你可以在我們的 Layer 1 上使用儲存網絡,但入口平台想用別的,也完全沒問題。
對 AI 來說,這種模組化尤其重要。因為在不同的系統裡,可能某些元件是最關鍵的,例如你需要一個特定的微調引擎,或一個特定的模型。那麼在 0G 上,你就完全可以選擇最適合的部分去搭配,我們的設計就是為此而存在。
律動 BlockBeats:數據可用性(DA)是當前區塊鏈領域競爭非常激烈的賽道,有 Celestia、EigenDA 等強勁對手。 0G 的 DA 方案最大的差異是什麼?為什麼您有信心說 0G 的方案在性能和成本上都優於對手?
Michael: 這沒太多可說的,因為其實挺簡單直接的,我們的效能提升了上千倍。
去年,我們能做到的吞吐量是 20 MB/s。而在共識層,我們預期可以做到 50 GB/s。而且這還可以繼續擴展,我們甚至可以建造多個共識層。實際上,這意味著可以實現無限的數據可用性解決方案。
換句話說,這讓你能在 Web3 上建立任何東西,即使是原本只在 Web2 上才能實現的應用,甚至包括 AI 的工作負載。例如 AI 資料中心的任務,通常需要數百 GB/s 甚至 TB/s 的效能吞吐量,我們也能 cover。
所以我們現在基本上就是:最快、效能最高、成本最低、同時也是最安全的解決方案。這一切源自於我們的架構設計,從第一原理出發,面對 AI 這種極端應用場景來思考與建構。
律動 BlockBeats:0G 的願景是「讓 AI 成為一種公共產品」。當前 AI 巨頭林立,您認為實現這一願景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0G 將如何一步步打破 AI 領域的黑箱?
Michael:我們面臨的最大挑戰在於,傳統的超大規模雲廠商(hyper scalers)玩的遊戲是盡可能多地融資,然後把大量算力堆進資料中心,用這些算力去訓練模型。但我們要玩的是另一套遊戲,讓 AI 成為公共產品。我們希望社群能夠主動參與,貢獻數據、貢獻算力,一起建構模型。
想像未來,社區裡會有數百萬個由專家打造的「專家模型」。例如,我不想用 Claude 來寫程式碼,而是和最懂 Solidity 的朋友們一起,專門訓練一個 Solidity 程式設計模型。我們把自己的資料和程式碼片段貢獻出來,訓練出這個模型。這樣的專家模型在各個維度上都能超越現有的最先進模型。
這完全不同於黑箱模型。像 OpenAI 或 Anthropic 這樣的公司,你完全不知道模型的資料從哪裡來,誰標註的,甚至連你輸入的 prompt 是不是被改動過都不清楚。我跟 DeepMind 的一位朋友聊過,他在那裡待了 15 年。他說因為某些倫理過濾機制,你輸入的 prompt 在發給模型之前就已經被修改了。也就是說,你輸入的提示詞甚至不再真正屬於你自己。
這些不透明的問題數不勝數,而用戶卻只能把信任交給一家公司,這就是黑箱化,非常麻煩。我稍後會在另一個問題裡再展開。
在 0G 的架構裡,一切都是透明的,完整的溯源(provenance),完整的可驗證性,清楚知道是哪個模型做了什麼,推理請求從哪裡來,清楚訓練過程如何進行,哪條數據帶來了什麼結果。正因為如此,你還能從這些模型主動剔除負面屬性。
這樣的價值主張在一些需要社會層級規模的 AI 應用中尤其重要,例如物流系統、運輸系統、機場等等。
律動 BlockBeats:0G 的技術團隊很強大,聯創 Fan Long 和 Ming Wu 都是業界知名的技術專家。您是如何認識他們的,在合作中你們是如何分工協作的?
Michael:我們最初的相識是透過我在史丹佛的同學 Thomas。我認識 Thomas 大概 12 年了。 2022 年,他打電話給我,說:「嘿,Michael,我們過去幾年做了不少加密相關的投資。5 年前我投了一家公司叫 Conflux。Ming 和 Fan 想要做一些更俱全球規模的事情,你有興趣見見他們嗎?」我說聽起來很有意思,可以聊聊。
接下來我們大概花了 6 個月在進行 Founder Dating。最後我得出的結論是,這是我遇到過的最優秀的工程師團隊,我們必須一起開始做些什麼。這就是 0G 的起點,時間是 2023 年 5 月。
最初一切都是從團隊出發的,我們還在探索每個人的專長。 Ming 現在是首席科學家(Chief Science Officer),主要負責科研方向;Fan 則更多思考更深層次的研究問題,以及協議該往哪裡推進;我自己也會涉及一部分研究,但更多精力放在確保研究成果能夠落地生產,並以此為核心來擴展整個工程團隊。
而我所承擔的角色,則是明確我們要建構什麼、我們對 AI 現實發展的願景是什麼。
律動 BlockBeats:0G 的生態系在早期就吸引了超過 300 個項目。在您看來,什麼樣的 AI 應用程式是您最期待在 0G 上看到的?能否為我們描繪一兩個具體的場景?
Michael: 我的看法是,現在說「我在做 AI 公司」,就好比 2000 年的時候有人說「我在做一家互聯網公司」。最終,世界的每個面向都會被 AI 融入。對我來說,任何涉及 AI 的用例都可以連接到我們的基礎設施。這是我們最根本的視角,AI 終將滲透一切。
具體場景上,考慮到 Web3 目前主要仍集中在交易和金融領域,我認為最先爆發的應用會是金融和交易相關的。
例如,現在已經有一些鏈上智能體(Agents),它們會幫用戶在不同鏈之間尋找最優收益。這非常有用,因為作為個人用戶,我並不想每天去查 100 條鏈、看各種收益指數,來比較哪一個收益最高、哪一個在收益和安全之間更平衡。而 AI Agents 可以自動幫我完成這些任務。
再比如,更複雜的投資策略,例如透過循環貸(Looping Strategy)來提升收益。假設我持有一個代幣,代表的是一個年化 12% 收益的市場中性對沖基金,我可以透過加槓桿的方式來放大收益。但問題是,我需要隨時盯著,確保槓桿成本不會高過對沖基金的收益。而 AI agent 完全可以自動完成這種監控,並在必要時再平衡。它甚至可以自動發現不同鏈上最合適的槓桿機會,而這些通常需要大量人工參與。
未來我們甚至不需要給它逐條具體的輸入。你只要告訴 Agent:「做我的投資組合經理,這是我的風險偏好,這是我希望的回報率”,然後它就能替你操作,像一個私人金融顧問一樣。隨著時間推移,我們會看到更多使用者體驗被 AI 抽象掉,複雜的流程都會自動化。
首先,我最期待的就是這些金融和交易場景。之後,我希望看到更多“社會層次”的應用。比如說透過智能體來管理我的工廠。那我該如何確保它保持合規、如何確保它能按時交付,這些將是未來需要解決的新挑戰,但最終都會走向那裡。
律動 BlockBeats:您曾提到,在以太坊上運行一個簡單的 AI 模型可能需要 100 萬美元的 Gas 費。在 0G 上,類似的成本大概會是多少?效能和成本的巨大優勢,將為 Web3 帶來哪些全新的可能性?
Michael: 在 0G 的共享基礎設施上,我們能以最高降低 95% 的成本來交付 AI 應用。這意味著,即便是規模較小的企業,也可以在這裡訓練自己的模型、運作推理。這創造了全新的可能性,他們能開發出小型的專家模型,供他人使用,從而再次推動 AI 成為公共產品。
舉個例子,如果我沒記錯的話,Grok 的訓練使用了大約 200,000 片 H200,而每一片 H200 大約有 60 TeraFLOPS 的算力。相比之下,一台 iPhone 只有大約 2 TeraFLOPS,也就是說兩者之間有 30 倍的差距。
換算一下,Grok 的訓練相當於用了 600 萬台 iPhone。如果真的能調動 60 億台 iPhone 的算力,會發生什麼事?這就是上千倍的運算能力提升。你能建構更大的模型嗎?能。你能建構更多的專家模型嗎?當然能。一旦所有人都參與進來,你的算力總量就會顯著提升,因為它是跨社區共享的。
通常算力的瓶頸在於成本。但在這裡,不僅在性能上會有優勢,而且在安全性上也更高。因為你不需要在 AI 資料中心旁邊配一個核電廠來滿足能耗需求,而是可以把負載分佈到整個網路上。
這就是共享式架構能帶來的新可能性。
律動 BlockBeats:能否介紹一下目前的共識機制 CometBFT,以及路線圖中提到後續會過渡到的 DAG 共識,這一轉變將為 0G 的性能帶來多大的提升?這背後有哪些技術挑戰?
Michael:CometBFT 本身並沒有太多亮點。我們對它做了大量修改,打造出更簡潔的架構,讓每個分片都能運作 CometBFT 共識機制。目前每個分片能做到大約 11,000 TPS,而且是完全相容的。我們只花了幾個月就完成了設計和落地。
接下來,如果再加入類似 DAG-based 機制,我們預期每個分片的效能可以提升 10 倍,足以承載大規模的 Web2 應用。例如,一個分片可以支撐 WhatsApp、Facebook,或是在中國的微信這樣的體積。
這樣一來,任何人都能在 Web3 上建立他們想要的應用,就像在 Web2 上開發一樣,但成本更低,性能相當。
當然,要實現這一切還有很多技術挑戰,需要非常硬派的系統工程工作。例如在多共識機制下,我們必須確保每個共識機制都能維持正確的安全狀態;我們要確保驗證者擁有相同的共享質押;同時,還可以透過再質押機制,例如從以太坊或其他鏈引入額外的安全性。這些方面都還需要進一步解決。
另一個挑戰是,我們希望未來能實現「任何 iPhone 或任何消費級設備都能參與 AI」,但以現有的驗證方式還做不到。我們現在依賴的是 TEE(可信任執行環境),而 TEE 只存在於高階伺服器顯卡里,像是 H100、H200 之類,一般消費者設備根本用不起。
如果想讓 iPhone 這類裝置也能參與,就必須有新的軟體層或不同的驗證機制。我們已經有了一個早期的嘗試,結果很有前景,目前的開銷大概是 TEE 的 2.4 倍,但可以推廣到 iPhone 或邊緣裝置。
所以這其實是我們在 AI 側必須要解決的技術難題。換句話說,我們總是兩條腿走路,一邊是區塊鏈側的深度突破,另一邊是 AI 研究側的深度突破。只有在這兩個維度上都取得進展,才能真正推動我們所描繪的未來。這也是讓人興奮的地方。
東西方文化的深度融合
0G 計畫最引人注目的特色之一,就是其深厚的中文社群淵源。這不僅體現在團隊組成上,從 CMO Ada 到技術核心 Fan Long、Ming Wu,都有著深厚的中文背景,更體現在專案的文化理念和發展策略上。
這種東西方文化的融合並非偶然,而是源自於 Michael Heinrich 本人的跨文化成長經歷,以及他對不同文化優勢的深刻理解。從熊貓吉祥物的選擇,到與中文開發者社群的深度合作,0G 正在建立一個真正全球化的去中心化 AI 生態系統。
律動 BlockBeats:0G 與中文社群的連結非常緊密,0G 的 CMO Ada 來自中國,也是您的太太,這種家庭背景是否影響了 0G 對中文市場的看法和策略?
Michael: 確實,這影響了我對中國市場的看法。因為在西方市場上行之有效的方式,例如溝通的方式、談判的方式,在中國市場並不奏效。對中國社區來說,能建立信心的東西,往往和西方社區不一樣。
在這方面,我們的努力非常關鍵。例如引進了合適的團隊成員,像是 JT、Vanessa,還有很多其他夥伴,來支援不同的環節,共同打造一個真正對 0G 充滿熱情的社群。
同時,我們在中國也在推進教育和課程,幫助人們在參與和貢獻網絡的過程中不斷學習。這樣一來,社區成員會有一種共同的「所有權」感,一起推動未來的發展。這就是我們在中國的戰略。
律動 BlockBeats:您和 Ada 在工作和生活中是如何配合的?一位是德裔背景的 CEO,一位是華裔背景的 CMO,這種跨文化組合在團隊管理和市場推廣中,帶來了哪些獨特的優勢或有趣的火花?
Michael: 我認為這是非常互補的,因為我們把東西方的優勢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互補。
從我的角度來看,一個獨特的優勢是我有時會願意下更大的賭注。例如,當 Kaito 剛推出時,我們是最早登上排行榜的公司之一。當時我直接說,我們要全力以赴,大力推進,在社區上進行大量投入。結果我們第一次拿下了投票排行榜的第一名。像這樣敢於「all in」的做法是我的風格,她的風格相對更謹慎,更偏向風險規避。
不過我同樣很欣賞她的這種視角。因為在某些情況下,冒進並不是好事,循序漸進、慢慢建立聲譽才更合適,尤其是在不同文化環境中。這樣的動態很有價值,因為我們能夠不斷辯論,在具體情境下,什麼才是正確的選擇。她的思路讓我更了解「全球化思考,在地化行動」。
這確實是個很好的總結。例如,在美國或德國市場上,我會更有發言權;而在中國和亞太市場,我則完全信任她的判斷與處理方式。
律動 BlockBeats:0G 的吉祥物是一隻非常可愛的熊貓。我們知道這個創意源自於您「功夫熊貓」的暱稱。能分享一下這個暱稱的由來嗎?為什麼選擇將這個個人化的故事融入品牌影像中?
Michael: 我們一起看了《功夫熊貓》,都非常喜歡。從那以後,她就開始叫我「功夫熊貓」,因為我練少林功夫。順便說一句,我在電影上映前就已經開始練功夫看功夫表演了。總之,可能也因為我骨架比較大,所以她叫我「熊貓」。而我對她很痛,所以我叫她「小兔子」。
我們覺得把熊貓當作品牌吉祥物會很有趣,因為這個稱呼有這樣的來源。我們始終認為品牌必須是個人化的,品牌不能脫離創辦人,因為創辦人決定了公司很大一部分的基調,它的氣質、人們如何交流、外界如何談論這個品牌、品牌代表什麼。所以把熊貓融入品牌顯得很自然。
熊貓本身也代表和平與幸福。它同時也是中國的國際形象吉祥物,象徵友好關係和尊重。在亞洲,尤其是日本和韓國,人們特別喜歡熊貓。只要有熊貓相關的東西,大家都會非常興奮。我們甚至構思了一個「太空熊貓」,希望能把這種快樂、興奮、和平與友善帶到太空,延展到 AI 共存的未來。
社群對熊貓的反應非常好。事實上,最初的熊貓設計是由社區成員創作的。我們舉辦過一次比賽,從社區作品中選出了一個優勝者。
律動 BlockBeats:0G 的技術團隊與中國的 Conflux 專案有很深的淵源,這帶給你們哪些影響?
Michael: 我們與 Conflux 有著深厚的起源。 Conflux 既是 0G 的投資方,也是顧問,對我們產生了非常正面的影響。因為無論是 Ming 還是 Fan,他們在去中心化系統方面都有非常深厚的專業背景,不僅在技術層面,也在 AI 領域都有研究經驗。 Ming 在微軟研究院時也編寫過一些最早的 AI 演算法。
有了這樣的技術專長,再加上在 Web3 行業五年的實踐,對我最初作為創業者的成長非常有幫助。我自己大概從 2013 年就開始進入這個領域,當時透過 Coinbase 買了第一筆比特幣。之後也參與了許多 ICO,例如在 Binance 的 ICO 時買入了 4 分錢成本的代幣,取得了非常好的收益。
在那個階段,我就知道自己未來一定會加入 Web3,因為我喜歡這種創造力的爆發,想成為這擴張環境中的一部分。對我來說,這既在創業的角度產生了正面影響,也幫助我在 Web3 成長路徑上持續前進。
在顧問服務方面,Conflux 的工程師也會支援我們一些核心技術的研發。這對加速進度非常有幫助,因為要打造高效能的分散式系統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這種程度的專業能力,全世界大概也只有上千人具備。而我們團隊就有大約十個人,再加上 Conflux 的支持,我們能夠更快地推動技術落地。
律動 BlockBeats:你們也和 HackQuest、TinTinLand 等機構合作,啟動了大規模的中文開發者成長計畫。為什麼如此重視中文開發者?您對中文開發者社群有怎樣的期待?
Michael: 如先前所提到的,我們的理念是「全球化思考,在地化行動」。從開發者社群的角度來看,中國有許多開發者對 Web3 技術和 AI 技術都非常關心。我們希望能與全球最優秀的開發者合作。而考慮到我們的文化背景,自然就會更容易吸引中國開發者,並與他們建立更深入的合作。
因此,我們希望在中國找到最適合的合作夥伴。在黑客松等活動中,我們確實認識了非常優秀的夥伴。我們也持續看到,中國有一個龐大而充滿活力的社區,可以與我們一起長期建設,在 0G 上創造出真正有意思的應用。
律動 BlockBeats:對於一個想要在 0G 生態中 BUIDL 的中文開發者,您有什麼建議? 0G 會為他們提供哪些獨特的支援?
Michael: 開發者的入口是 builder.0g.ai,還有我們的技術文件網站 docs.0g.ai。這是最初的起點,你可以在這裡了解 0G 的運作機制、能建構什麼,以及你感興趣的方向。
除此之外,我們還有一些額外的支援。一個是 加速器計劃,會有 Demo Day,你可以在上面展示、融資。另一個是 Guild on 0G 計劃,它更像是客製化支持,如果你有某個具體想和我們一起開發的項目,我們會為此提供資源和幫助。
此外,我們還有一個 8,888 萬美元的生態基金,用於支持和培養這個領域裡最優秀的創業家和建設者。隨著時間推移,我們會推出更多項目,真正從早期階段就扶持開發者。
如果你還沒準備好加入這些計劃,也可以先參加我們的黑客松,透過這樣的方式加入進來。然後我們會支持你經歷完整的專案生命週期,直到在 0G 鏈上建立一個高度可擴展的產品。
我對開發者的期望是,他們能逐步走完整個過程,最終成為最好的自己,成為最優秀的人才和建設者。而這一切,將會透過 0G 的平台,以及我們的輔導、支持和資金來實現。
律動 BlockBeats:未來,您希望 0G 在中文社群使用者心中,是個怎樣的品牌形象?一個技術領先的公鏈之外,還希望傳遞怎樣的文化和價值?
Michael: 除了技術能力之外,我們還希望在文化與價值觀上,真正體現並傳達一種「在一起」的感覺,就像家庭、社區,以及對社會的責任感。
我們不想只在口頭上談「安全、透明的 AI」,而是要把它內化為我們的身分與日常行為。為此,我們必須與社區共同建設,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打造一個人人參與的 AI。我們不認同那種由少數幾家公司控制全部 AI、進而幾乎控制整個商業並獨享其利的未來;那樣會帶來大規模的崗位被取代,人們被迫依賴 UBI。
我們更希望看到的未來是,人們向 AI 做出貢獻,可以貢獻算力,也可以貢獻數據,或以其他方式參與,並由此獲得回報。這樣,人們工作的目標將不只是「謀生」,而是為了自我實現(不論這對每個人意味著什麼)。
也許有人貢獻了自家的算力或數據,而他/她一天最想做的事情就是烹飪,那正是 TA 的生活樂趣。我們完全應該讓這種生活成為可能。對社會負責的深層意識,是我們整體路徑的一部分。我們希望充當前鋒,推動所有人過更富足的生活。
我認為應該把 AI 當作一個加速器,讓我們能做得更多、達成更多。把它當作一個組件來對話、腦力激盪與協作;同時思考如何確保這種組件不是你的敵人,而是始終站在你這邊。這也需要教練式的方式來思考與回饋。所以我們現在就要投入實踐。把「學習」當作一項技能,去學習 AI,學習如何以去中心化方式提供透明性與可驗證性,也學習如何與它們協作/應對;不管我們今天是否準備好了,明天都會到來。
最好是現在就做好準備並開始學習,擁抱它、與它共創,而不是被動應對,讓它掌控我們的生活。
律動 BlockBeats:您認為去中心化 AI 在未來會有怎樣的社會地位?
Michael:我認為未來不同類型的 AI 模型會並存。
例如在你的手機等邊緣設備上,可以運行輕量 AI,如果只是訂餐廳、訂行程,這樣的任務完全可以在本地完成。如果是更複雜的工作,例如寫研究報告、做深度搜索,那你還是會用中心化 AI。而一旦涉及高度安全的場景,例如物流系統、機場調度、政府或行政系統,就必須使用 去中心化 AI,因為只有它能保證安全、透明和可驗證性。
所以,我們看到的未來模式就是共存。
但在社會層級的 AI 應用中,尤其是那些無需人工輸入、能自主決策的主權型 AI 智能體,它們必須運行在去中心化 AI 的軌道上。原因很簡單,只有在去中心化 AI 上,我們才能建立協調機制。這樣,當某些智能體展現出不良特徵,或出現負面行為時,我們能迅速採取行動,例如透過懲罰機制削減其激勵或直接移除,迫使它們回到符合預期的行為模式。
去中心化 AI 的新起點
透過這次深度對話,我們看到了一個完整的 Michael Heinrich。從在東柏林圍牆長大的孩子,到在史丹佛開設意識課程的學者,再到如今投身去中心化 AI 生態的創業家。他的人生軌跡看似跨越了多個領域,其實有著清晰的內核,即對人類潛能的探索,對技術與人文關懷的結合,以及對建構更美好世界的執著。
0G 的意義,也遠遠不止於技術層面的突破。在 AI 日益集中化、黑箱化的背景下,它提出了「讓 AI 成為公共產品」的願景,這不僅是一個技術項目,更是一場關於未來社會形態的實驗。
隨著主網正式上線,0G 進入了新的階段。它已擁有超過 100 個生態夥伴、8,880 萬美元的生態基金,以及一支融合東西方背景的團隊,為實現宏大願景奠定了基礎。更重要的是,0G 與中文社群的深度連接,使其在全球化進程中具備了獨特優勢。在一個愈發需要跨文化協作的世界裡,0G 正展示如何結合不同文化的力量,創造更大的價值。
正如 Michael 在訪談中所說:「現在就做好準備並開始學習,擁抱它、與它共創,而不是被動應對,讓它來掌控我們的生活。」這不僅是對 AI 未來的思考,也是對所有人的提醒,在科技快速演進的時代,主動參與和塑造未來,比被動接受更為重要。
本文以 0G Labs 創辦人兼 CEO Michael Heinrich 的獨家專訪整理而成。專訪於 2025 年 9 月進行,正值 0G 主網上線之際。
免責聲明:文章中的所有內容僅代表作者的觀點,與本平台無關。用戶不應以本文作為投資決策的參考。
您也可能喜歡
加密貨幣概況:市場平靜,43億美元的BTC與ETH期權到期

在強烈的空頭情緒下,PI可能跌破0.20美元

隨著CFTC與FDIC領導層接近確認,美國加密貨幣監管日益收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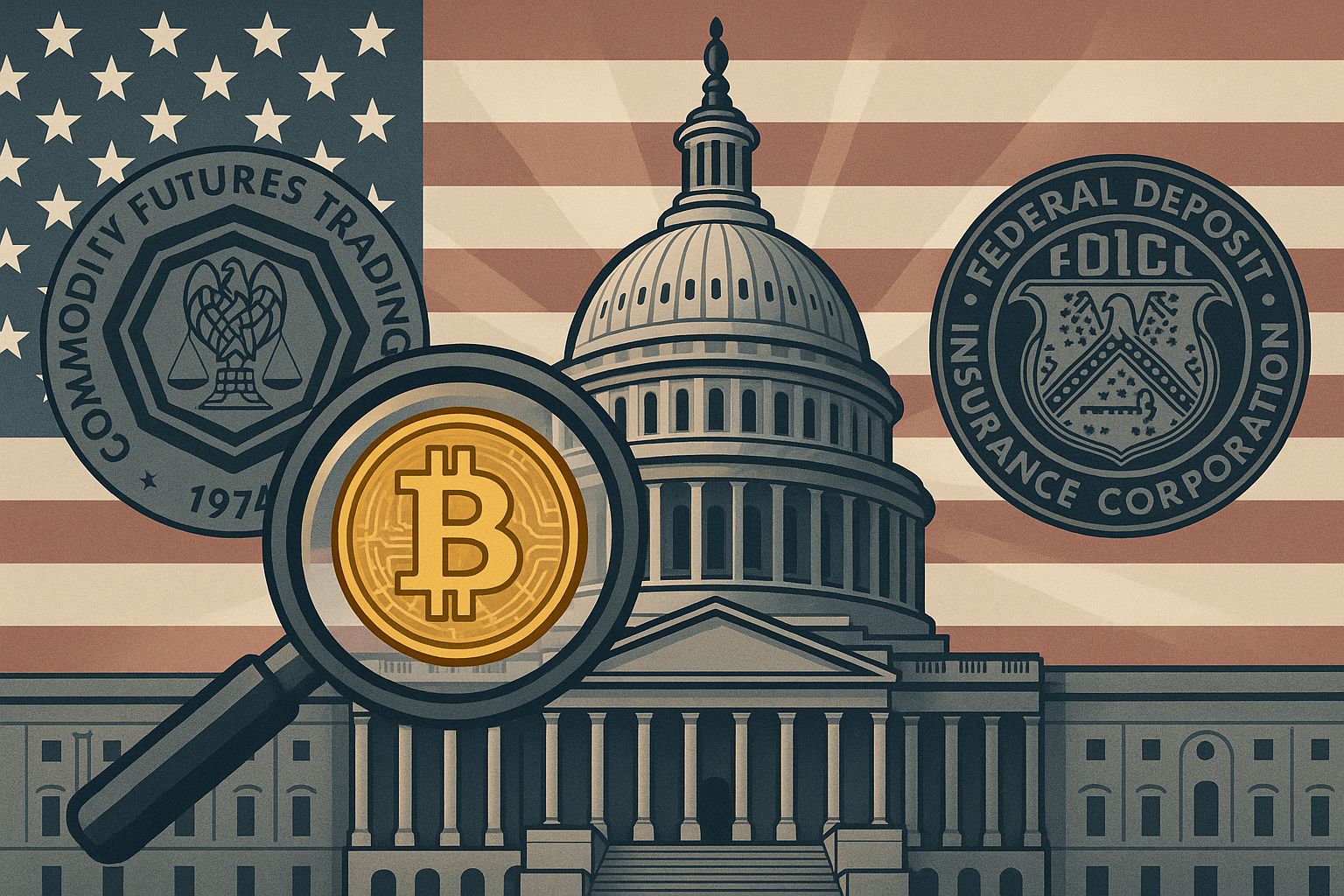
以太幣可能在多頭動能停滯時重新測試3千美元:請參考預測

